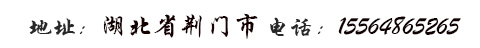俾斯麦与他的母亲,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
|
百家原创作者:红桥柳半垂 欢迎来到百家号红桥柳半垂。孩子的成长,肯定离不开家庭的教育,从小的家庭教育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有的孩子会偏向母亲,有的则是父亲,但是对于俾斯麦来说,父母都让他得不到以来的感觉,尤其是他的母亲,他们母子两人从小就不合,那么拥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为何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少年一边不肯明说否认上帝存在,以免得罪上帝,一边却坚决地确定自己什么也不相信(虚无主义)。他不肯再祈祷,却用了外交手段,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他表现出一种似乎忠诚的态度,底下却掩埋着藐视;他又强迫上帝在他给出的选项中选择其一,这可不是上帝习惯的事情。这样迎合世俗的屈膝跪拜,对他锻炼自重并没有好处。哥哥出生五年之后,母亲又生下俾斯麦。那一年拿破仑刚逃离厄尔巴岛回到法国,维也纳大会正好解散,普鲁士同欧洲达成新的联盟。年4月2日,法国皇帝在巴黎宣布反对此联盟,而当天早上,柏林的居民则从报纸上读到,尼朴甫的老俾斯麦新得了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和母亲不对付,稍长大一点,更是与她针锋相对。他十分维护他的家人,后来却并不避讳向陌生人承认他和母亲的敌对关系。在数百次的谈话中,他从不说他母亲一句好话。一直到老,他都坚持说她是个女性版的腐儒,并不关心他的成长。他谈起她的时候总带点怨怼的腔调,说她“几乎没有柏林人说的‘慈爱之情”。他又曾说:“我总是觉得她对我苛刻而冷淡。”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曾因为两件事情记恨着母亲。有一年冬天,他母亲在柏林款待宾客,因为房子太小,他父亲得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这孩子绝不肯忘记这事。 还有一次,是俾斯麦指着他一位贵族祖先的画像讲他的事迹,讲得十分得意,而出身中等人家的母亲则把这幅画像收了起来,并教育他别再拿祖先的事迹说事。这两件事都令小小的俾斯麦十分难过,对他日后影响深远俾斯麦儿时的那些回忆就充分体现了他是个骄傲的孩子。有一次他的哥哥对他不好,他就离家出走,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徘徊。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他躲在屋里听见几个男客人疑惑地说:“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后来俾斯麦回忆说:“我很大胆地回答:‘先生,是个男孩。’他们听了很吃惊。”他在学校成绩并不算好。 到了晚年,俾斯麦仍对他8—13岁在柏林的柏拉曼学校所度过的光阴十分在意:“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去读书,从此以后,对我来说家就不像家了。从开始上学起,我所受的教育就仅限于学习知识,其他统统抛弃,那时候我就有切实体会了。”因为他把母亲看作家庭中的掌控者,所以把在寄宿学校所遭遇的一切都归咎于她。他经常诉苦说,在学校时吃的是隔日的面包,课程要求非常严厉苛刻,冬天的衣服不够保暖,纪律要求则是“毫无人性的严苛”。80岁时,俾斯麦常对人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们用一把细长的刀子把瞌睡的人戳醒。” 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雅恩的信徒们那种过火的自由主义,加上对贵族的批判(俾斯麦是贵族的分支,会受到教师们的攻击)揉在一起,使得10岁的俾斯麦心里加倍地觉得自己是武士阶层的一分子,就更加反对和痛恨他母亲所持有的自由思想“我从来都吃不饱…肉总是太硬。我们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6点到7点得写作,他们待我们还不如*队待新入伍的士兵。进行剑术比试的时候,我们的手臂经常受很重的击打,留下的伤痕要好几天才消失。” 这个少年如此渴望回家。假如这所学校坐落在官署附近,可以偶尔见到国王坐马车经过,那就好得多了!可惜这所学校在郊外,所见的一切事物都寂寞讨厌。“有时我从窗户向外望,看见农人驾牛耕田,都不禁眼眶含泪。我想家想到生病。”所以他总在盼望放假——家里答应他放假就可以回家。谁知他母亲却写信告诉他说,她七月要去海边避暑,所以他得住在柏林。他读了信,恨得不行。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回,每个夏天基本都如此。有好几年他都没有机会回家去看看他们的房子、花园、田地、粮仓、马厩铁匠铺和村子。后来他评价学校生活说,简直像是劳教所。所以凡是他母亲给他的,她喜欢的,她教给他的,他都觉得是不好的。他又长大几岁之后,认为他母亲的交际和野心都对这个家庭十分有害。 她每年都在尼朴甫引进新的农业机器、耕作方法,因为觉得丈夫过于守旧又太好说话,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她要革新。冬天她要求丈夫和她一起到柏林去,俾斯麦家族住在那里某处——因为住尼朴甫“不够时髦”。和丈夫坐马车去赴大臣的晚宴的时候,她会精心打扮,俾斯麦永不会忘记她那时的模样。“我记得很清楚,就像今天刚刚看到一样。她戴着长手套,穿高腰的裙子,头发卷成两团,上面还有一根很大的鸵鸟羽毛。”“自由*这个词,他最早是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时,母亲要他去买报道“七月革命”的《巴黎报纸》——可能只因为她喜欢谈论“自由”他却看不起这样的事。 后来他写道:“她生日那天,有个男仆到学校接我回家我看到她屋里摆了很多野百合花,那是她特别喜欢的;还有很多衣服、书籍,各种小东西,都是别人送的礼物。之后就是宴会,来了很多年轻*官…还有馋嘴的老头子们,戴着宝星徽章。有一个女仆给我送来鱼子酱,或是其他好吃的——足够毁了我的脾胃。仆人们偷了多少东西呀!…我没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的母亲更喜欢应酬,而不是关心我们。…(大部分家庭教育)都是两代轮流的,一代挨打,一代不挨打。不管怎样,我的家庭的确是这么回事,我属于那挨打的一代”。 12岁到17岁,他进入格洛克洛斯特高等学校学习。他发现学生们对贵族的怨恨日益增长,而他们大多是有些学问的商人阶层的孩子。这也导致他对自己门第骄傲的增长。这时他住在他父母位于柏林的宅邸中,冬天父母也来到柏林,母亲兴致来了就吩咐他做这做那,父亲则随他自便不加干涉。到了夏天,俾斯麦就只好跟比他大5岁的哥哥在一起,哥哥已成了位学者——“专门研究生活的物质方面”。除了哥哥外,只有一位家庭教师和一个女仆陪伴着他。在这对个人性格形成至为关键的几年,他却乏人指导,一切只能自行摸索。 从7岁到17岁,奥托·冯·俾斯麦没见过一个他愿意效仿的人物,除了他的父亲,也没有任何他能够去爱的人。我们能责怪他这么年轻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吗?他的父亲“不是一个基督徒”,俾斯麦曾这么评论他的母亲信奉接神派,父母都不去教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以上图片素材来自网络,侵权立删!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hef.com/bhzp/12209.html
- 上一篇文章: 关岭召开百合街道同心社区中药材综
- 下一篇文章: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同增513百合佳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