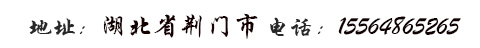异国风情冯磊ll中亚印象
|
zhongya中亚印象----冯磊 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的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中亚五国,是当今世界地区间经济发展最具潜力与活跃的地区之一。 年6月,我随旅行团到中亚地区的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旅游,一路走一路看,所到之处的发展速度之快令我惊叹不已;同时二十多年前的七八年时间里,我以四师外贸公司和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职员身份,在中亚地区断断续续常驻工作的所见所闻,便历历在目浮现眼前。 走39号公路 年12月的一天,我随四师商务考察团从霍尔果斯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阿拉木图一家公司主管到口岸接我们。 他是哈萨克族,二十七八岁,名字叫吐尔别克。黑黑的头发,脸上的线条有力而充满生气,个子不高但英武壮实,很像中国第一个奥运会举重冠*吴数德。他跑前跑后溜溜儿地帮我们办完入关手续。 坐上车,吐尔别克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走的这条路是39号公路,起点是霍尔果斯(境外),终点是莫斯科;长度公里,中亚境内约公里……”这相当于中国的一级公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就建成了,令我惊讶。 汽车在宽展的39号公路上疾驶,发动机的轰鸣声,车轮与地面摩擦的扎扎声,和着车窗外时而平整肥沃的农田,时而绿绿的草地和吃草的羊群,从眼前一一驶过,暗合着我初出国门的激动心情。 进入雅尔肯特市吐尔别克说:“雅尔肯特市区面积约五平方公里,人口约三万,哈萨克族约70%,俄罗斯族约15%及其他民族……” 小城建筑多为三四层的楼房;隔几条街就有一个小公园。吐尔别克带我们到一个普通居民小区转了转。他说:“哈萨克斯坦每个城市的住宅小区基本都像这个小区一样,建有停车场、健身场、面包房、小市场;绿化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在当时令中国人十分羡慕。 离开雅尔肯特市我猛醒过来,一幅幅悲愤耻辱的历史画面浮现眼前。我心情复杂而愤懑地对同事说:“这么美丽富庶的地方本来就是中国的。今天我们沿途看到的河流、山川和草原,正是年晚清*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被强虐瓜分的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一部分。” 我的心久久不平静,像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凌凌乱乱地缠绕。一百多年前我的祖国母亲那段屈辱历史,是用一具羸弱的身躯挣扎在十九世纪的黑夜,悲痛地咽下满目忧伤在屈辱和苦难中徘徊了一百年! 我含辛茹苦的母亲啊!我鲜血淋淋的母亲啊!你匍匐在黑暗那悲怆的一幕,如云翻滚在我们炎*子孙的心头怎么都挥之不去! 一个孱弱的被鸦片麻醉的民族,一个松散的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一个彼此争斗木然地忍受外侮的民族,怎么不令人爱恨呢? 我一边咒骂强盗沙皇;一边咒骂晚清*府。这是饱受列强侵略、蹂躏和欺凌的咒骂!这是牢记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的咒骂! 但是,屈辱也是力量的源泉!从三元里到*花岗,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来雪耻这一百多年的屈辱。那是一个热血喷张的时代!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一个民族精神崛起的时代!直到最后一个大个子湖南人,用一条井冈山的扁担,挑起了一百多年的不幸——他就是伟人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汽车沿39号公路向西风驰电掣地跑了约40公里,公路突然像驶入大江的入口,宽展起来。吐尔别克坐在副驾驶位子扭过脸看我们有些疑惑的表情朗朗地说:“这是紧挨着公路的飞机跑道。上世纪六十年末苏联和中国随时会打仗,苏联便依托公路修建了这条临时*用机场。现在它早已经失去‘*事要塞、扼守咽喉’的意义,连跑道旁的无线电起降设备也看不到了。但这些冷战产物应时应景地成为那个时代苏联人在这个纯净之地留下来的历史物证、线索和痕迹。” 哦,吐尔别克不仅年轻、帅气、干练,还有不少外交辞令呐。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四师商务考察团在阿拉木图 左二、本文作者,左四、四师外贸公司总经理袁伦正,左五阿拉木图常务副市长布拉特 离题万里地说,后来我每次走39号公路坐在追风逐电的汽车上,风光绮丽的崇山峻岭、一马平川的图兰低地平原,雄浑粗狂的埋藏着丰富地下资源的黑土地从我眼前一一掠过,令我羡慕不已。 现在39号公路已升级提速。成为新“丝绸之路”连接欧洲西部至中国西部公路交通走廊的枢纽。年经39号公路往返中国与欧洲的货物达万吨;时间由海运的45天缩短为陆运的11天。 在场长家做客 车过了“*用机场”向西约一小时驶入一个大镇子。吐尔别克说:“这里是恰布奇盖国营农场,我们现在去这个农场场长家吃饭。” 车在恰布奇盖镇子七拐八弯地往前走,我一眼看出这个镇子很美,美得就像大师晕染的水墨画,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妙不可言。 车在一大宅院前停下,走出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男人,吐尔别克说,他就是场长居马洪。他是哈萨克族,高大魁梧、五官端正,洋溢着微笑,说话瓮声瓮气的直拢音,浑身散发成熟男人的光彩。那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睛格外乌黑明亮。他的眉毛黑而长令我吃惊。眉毛不是头发,任它去长不会有人理掉。可他的眉毛为何长得那么浓密黑长? 居马洪场长的宅院有足球场大,一座俄罗斯风格的二层小楼坐落其中。一缕缕炊烟在楼顶上空飘荡,上上不上去,掉掉不下来,仿佛恰布奇盖的众多居民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鹤立鸡群的建筑供献香火。 进入居马洪场长家里,他主动带我们楼上楼下地看看。从这一点让人一眼看出居马洪场长非常开朗豁达,把我们当朋友了。 每间房子无一例外是纯正的哈萨克族的传统装饰和摆设。 我对居马洪场长家总的感觉是,建筑风格着墨于内敛的低调奢华,不矫揉造作于过度装饰;透过选用装饰材料和家具前卫时尚,既质感地激活室内的整体空间,又不乏古朴清雅的派头;既呼应了建筑本体,又显现主人干脆利落的生活态度和权力身份的象征。 主客厅,一张放大的居马洪场长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握手的彩色照片特别醒目。居马洪场长说:“这是总统来我们农场视察的照片。” 那天,居马洪场长还请来几位当地客人。宴会前他十一岁的小女儿玛利亚端着油果,不停地劝客人吃,全然没有陌生和羞涩感。 当奶茶、馕、馓子、酥油、熏生鱼、黑麦面包、鱼子酱等俄式菜肴上齐后,一盘*灿灿油滋滋的烤全羊端上来,然后是一托盘油汪汪的抓饭;那规格足以招待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主人请让过后,十几只大手就一涌而上,接着一些人的嘴角便流出了油汁。 居马洪场长爽朗地说:“男人要像狼那样吞咽,要像虎那样的肚腹。在哈萨克人家里作客,狼吞虎咽的人受尊敬!” 我吃了一口烤全羊,哇,汹涌澎湃的香味就铺天盖地地刺激我的味蕾,它对健壮的胃口是何等地难以抗拒啊! 这架势人都还没有吃就把气氛烘托出来了 大家都用手抓着吃。这种吃法容易让人找到与食物柔软的切合点,恰如哈萨克人祖祖辈辈在青草飘香、牛羊散落其间的那种生活环境。大盘盛饭、大块吃肉和大碗喝酒的习俗,即使再拘谨的性格,也会变得粗矿而豪迈起来。这时你好像跟优雅就隔着一道门槛了。 继续吃,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酣畅淋漓地吃出了豪气!吃出了战斗力!吃出了难忘!难怪美食家萨瓦兰说:“人类是所有动物中唯一能够在不感到饥渴的情况下享受吃喝的快乐的物种。” 我挨个看了看大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为中哈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我们的父母儿女幸福干杯……当优美的祝酒词从每个人嘴里朗朗地说出,谁能推辞不喝呢?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没料到他们这么能喝,我们忘了他们是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没想到我们这么能喝,他们忘了我们是中国的汉族!但刚开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默契,彬彬有礼地喝;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观察、保持一种状态的均衡。当酒过三巡,喝着喝着“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的意味就出来了。 居马洪把西装一脱,白衬衫袖子橹到大臂上,递烟的动作很慷慨,手势幅度大。就像见到故乡人藏匿起来的乡音全袒露在外了一样。 按照餐桌礼性,上了抓饭就该唱敬酒歌了。我知道,在哈萨克家喝酒没歌不行,是对酒不尊重,就像哈萨克人闻到了酒香而不让喝一样。这时唱歌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情愫和高兴而不是为了好听。 印象深的是,恰布奇盖农场副场长叫谢尔盖,他三十四五岁,一双乌溜溜的眼珠,高高的鼻梁。他向女翻译打了个飞眼乐滋滋地说:“我呀,用汉语唱一首中国朋友人人都会唱的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哇,旋律多熟悉啊! 他的声音像干渠的水一样洪亮,音域像条田一样开阔。并用“鼻腔共鸣”的嘶吼唱法,一下子饱满力道地唱出了力量的呐喊。 第一次在外国听外国人为中国人唱人人会唱的中国歌,爽! 居马洪场长笑吟吟地说:“谢尔盖是混血儿,父亲是哈萨克族,母亲是俄罗斯族;毕业于塔什干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辞去在阿拉木图做音乐教师的工作来到恰布奇盖,三十岁就当我们场副场长了。” 哦,国外也存在专业不对口的事。我想起国内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一直没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记者采访他,他说:“严峻的就业形势有目共睹,能找着工作就很不错,耽误了就业机会比‘学非所用’还浪费。干成事是硬道理。没有最好的工作,只有最合适的工作。” 时间过得好快。大家在门前依依话别,像难舍难分的老朋友。 车开动了,我的胳膊从车窗伸出来,再见啦……达斯维达尼亚……汽车继续沿39号公路风驰电掣地行驶,车轮与路面摩擦扎扎地响声,暗合着我得意洋洋的心绪向阿拉木图驶去。 中国朋友来了 在中亚,去朋友家做客一定要带礼物,尤其是鲜花。像阿拉木图、塔什干这样的城市,几乎每个公交车站和地铁站都有花店。单数花,象征幸福、好运;双数花是祭祀亡者。*色花视为不忠诚。送酒,以红酒、白兰地和香槟为宜。客人进门要先向女主人问好。 主人接受客人礼物一般会当面拆开以示尊重。若是食品,就摆到餐桌上让大家分享。一般家庭的餐桌多为长方形。有客人时,在铺着精美钩花桌布的餐桌上摆着有丰盛的食物或一瓶鲜花。为每位客人摆好餐具:刀叉勺、餐碟和酒杯。叉子摆在盘子的左手边,齿尖朝上;餐刀摆在右手边,刀刃朝向餐盘。盘前摆上酒杯和果汁杯等。 年7月的一天,在塔什干我们受邀去一位乌兹别克朋友家,带了一束香水百合,一盒巧克力等礼品准时到达。男主人把我们迎进屋,女主人把鲜花插进花瓶中摆到客厅,他们四岁的女儿蹦蹦跳跳地接过我们送的芭比娃娃玩具。主人还为我们准备了筷子。吃饭的时候,男主人一边用筷子灵活地夹菜,一边大加赞赏筷子如何如何好。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的筷子走红世界,美味佳肴被筷子摆弄得服服帖帖。用筷子吃饭就像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了一样。” 外焦里嫩的烤羊排 乌兹别克人,一日三餐都喝茶。朋友来了主人都会问:“你喝茶还是咖啡?”说喝茶,主人就说:“好来!我这就把茶煮上。”喝茶或喝咖啡时,还要品尝糖果、糕点、果酱、奶油、蜂蜜和柠檬汁等。 印象深的是,哈萨克人好客、热情、开朗。那次,我在哈萨克斯坦塔尔迪库尔干办完事回宾馆,从小餐厅传来阵阵歌声。陪同我们的哈方公司代表叫居玛拜,他谦和地说:“我们去玩玩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是为我的朋友热斯别克的儿子一周岁的生日派对。” 我想,他或许只是客气话,便说:“我们去不合适吧?” 居玛拜干脆地说:“当然合适!哈萨克人在太阳下山后放走了客人,是跳进河里也洗不清的耻辱。”看他的眼神很执意、真诚。 四师商务考察团与客商在塔什干。右三四师外贸公司副总经理耿云奇,左二本文作者 居玛拜推开门爽朗地说:“中国朋友来了。”大家都站起来表示欢迎。居玛拜把大家一一做了介绍。我透过满房子缕缕烟雾打量热斯别克,他又白又胖,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穿一身哈萨克服饰,手腕上戴的“苏联*表”足有二两重。热斯别克手拿水果糖小心翼翼地剥开一半糖纸,一颗一颗递给我们,然后有点羞涩地端起酒杯说:“中国客人来了我非常高兴!为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干杯!” 另一位小伙子晃了一下脑袋,挺潇洒地把滑到额头上一绺黑发甩到头顶上说:“为了给大家点儿笑料我弹一段吉他,豁出去了,献丑了!”他一手扶琴颈、一手扶琴弦,餐厅里鸦雀无声,一曲轻松、欢快的旋律便从指尖弹出,像河水从高山流下,打动在场的人。 “下面请居玛拜用手风琴演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热斯别克满脸愉悦地邀请说。哦,原来居玛拜是有备而来。 居玛拜把手风琴背在前面,长带背右肩、短带背左肩,调一下袋子的长度,大步走到餐厅中央,乐滋滋地理了理头发,站姿挺拔。 手风琴一响就把大家震慑住了。演奏中,居玛拜一会儿歪着脑袋,一会儿眼睛低垂,一会儿摇摆身体,一会儿与大家交流目光,那如痴如醉的姿势、动作和表情,简直就像一个手风琴专业演奏者对艺术作品倾注了满腔热情和驾驭演奏的能力,一下子就把这首悠扬浪漫的名曲用手风琴演奏和手风琴优美好听、变化丰富的顿音、断音的欢快特色给无限地放大了。居玛拜演奏完,掌声似乎能把屋顶给掀翻。 即便,我不懂手风琴,但我感觉居玛拜演奏时的状态、力量的处理、风箱的运用和手指触键的力度都非常非常专业。 热斯别克乐滋滋地告诉我们:“居玛拜以前是塔尔迪库尔干州文工团的手风琴演奏员,拉手风琴是他的拿手戏!”哦,难怪呐。 我唱了哈萨克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我没有唱歌技巧,但音准。热斯别克现场编词把他的弄璋之喜及客人都唱了进去…… 这样严谨刻板 年6月我到中亚旅游,看到有些城市的邮局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大量信件和物流交往依然靠邮*系统来完成,这与先进国家的邮*形成鲜明反差。便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中亚国家常驻工作时,看到他们那种缓慢与保守的“排斥”、迅速与开明的“吸收”,“堂而皇之”地拖沓、办事效率低,令许多性子急的中国人抓耳挠腮和不解,同时也慢慢消磨着一些中国人身上的锐气的故事。 与卡拉干达钢铁厂客商在一起,本文作者左三 在中亚国家办事,应尽量避开节假日。他们一丝不苟地享受“休息权”,很少在节日里加班工作,向来到点下班;而中国人不管这一套,到点就是不下班,只要能挣到更多的钱,只要是老板看见或过后知道的,就坚决不回家,都能把惟利是图的资本家给感动哭了。 从一件小事一窥中亚老百姓细致严谨而刻板的生活态度:年12月的一天,我在阿拉木图走进一个小商店买东西,摊主用手指着立在摊位一角写有“AM9:00——PM5:00”的纸牌耸耸肩膀讪讪地说:“我闭店了,不能卖给你东西了,请原谅。” 我愣怔地望着摊主,把拿钱包的手缩了回去。我想表现得自然一些,咽了一口唾沫,但我疑狐的神情还是僵在脸上:一个小小的店铺还有精确的闭店时间,放着钱不挣,不可理喻,就这样我被“秒杀”了。领教了时间就是命令,早了晚了都不行。计时单位不是小时,而是分、秒;若在中国,有顾客来买东西,摊主巴不得挑灯夜战吶。就像资本家追求利润一样,否则这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我的同事,时任“新天国际”的俄语翻译陈新成后来说:“我们在塔什干有个乞丐的邻居。那天,我看他没像以前那样手捧要钱的盒子不停地与路人‘打招呼’,而是悠闲地坐在一条凳子上晒太阳,我主动递给他五个索姆。但我的善举却被他礼貌地拒绝:‘现在不是我的工作时间不能收你的钱,谢谢你。’他这种严谨刻板的态度和生活情趣,简直让我哭笑不得的同时,又令我感叹不已。” 据说,中亚地区有些乞讨是一种谋生职业,并非饿肚子要饭吃那么简单。但我从来没听说有乞丐靠行乞‘发家致富’的事情发生。 从餐桌上的礼仪常识,窥视中亚国家老百姓的性格品质。 中亚国家老百姓的饮食不尚浮华,正式宴会不过六七道菜,包括两三道凉菜,三四道热菜,一道汤。多是分餐式,各取所需,不会取食吃不了的食物。几十人同时就餐,没有把餐具碰得叮当叮当响的;没有拿着餐具指指点点的;没有把类似蛋皮、骨头、鱼刺、籽之类的东西直接从嘴里“啐”地吐到桌子上的;没有“吧唧吧唧”吃相的;没有吃饭掉饭粒,边咀嚼食物边说话或将双臂置于餐桌上的。 而是坐姿端正,把餐巾平铺在腿上。吃饭时从最外的刀叉开始用。如果是一道羊排,切下一小块吃,吃完了再切一小块;吃一块较大的食物,吃一块切一块,不会拿在手里啃着吃。留下的骨、刺等弃物,都放在餐桌边。吃东西时低头接近餐具,喝汤不是吸到嘴里,而是用汤匙送到嘴里。即便你的眼睛像照相机,如抠鼻、剔牙、挖耳、搓脚;打喷嚏不遮挡;哈欠来了无遮无拦、旁若无人地将嘴巴恣意地撑大再撑大等不雅习惯很少见。最叫我暗暗吃惊的是,吃过饭后桌布基本上整洁如初,没水印,没有渣,没油渍。他们喜欢用白桌布,每次用过的桌布都浆洗、熨烫,叠得整整齐齐像工艺品。你说这样累不累?不累!人家习惯了。若一个邋里邋遢的人,当然就累了。 从另个层面讲,虽然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不能过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hef.com/bhjz/9088.html
- 上一篇文章: 写给孩子们的诗中华诗词学会女子诗词工
- 下一篇文章: 穿成豪门倒贴女配温室里的小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