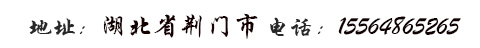唐珠有之藏珠记连载
|
5金泽:客居
拗不过赵耀,终于还是来了这里,客居。事实上,自从跟着爸爸来到郑州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在客居。无论是最初的老房子,还是后来一栋又一栋的新房子和更新的房子,又或者是住在各式各样的酒店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人。只是在赵耀这里客居,和在那些地方还不太一样。无论情愿不情愿,爸爸的房子总是和我多多少少有些关系,所以再客也有主的感觉,而酒店的宗旨不是“客至如归”么,谁拿钱谁就是主,主的感觉就更明显,哪怕只是短暂的假象。而在赵耀这里,客居就是客居,百分百纯粹的客居,一点儿不含糊的客居。
回想起来,最不客居的时候,就是跟着爷爷在老家的时候。记忆中的第一张脸,就是爷爷的脸,听到的最早的声音,就是爷爷的咳嗽声。生我的时候母亲难产而死,无从体会何谓母亲,爷爷就是母亲。按说姑姑更应该像是母亲,可是就是这么奇怪,我只觉得爷爷就是母亲。他也是父亲,有时候他也是我的老哥儿们……他就是一切亲人。做了一辈子的菜,他那赘肉累累的宽阔胸膛如一座微型厨房,走到哪里都散发着酸甜咸辣混杂交融的气息,馥郁深厚如老酒,这个胸膛就是我的家。
在这个家里,我生活了十五年,直到他死。回头想想,那真是奢侈的十五年啊。那十五年,也是我最快乐的十五年。我不是个省心的,从小讨厌上学,迟到旷课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回家早了,他问一声,我就撒谎,他总是眯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然后从鼻子眼儿里长长地闷出一声:
嗯——
我调皮捣蛋闯了小祸,老师叫他去学校,他黑着脸回来,我假装害怕,走着小步子,畏畏缩缩地靠近他,他撑不了多久,叹息一声,也就笑了。
他似乎早早就认了命,从不逼我学习,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都由着我。他的主要乐趣就两样:一是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二是带我出去找好吃的。可以说,老家附近的美食单品我们都吃遍了。只要是不太远的地方,一天能走个往返程的,他就会带我去。沁阳有一家店,专门做生汆丸子,我和爷爷第一次去吃的时候,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滋味,太鲜美了。博爱有一家炸枣糕的,是发糕,就两口子,一辈子就卖这个东西。油温啊,面的柔软度啊,他们就是把握得最绝。我一时兴起,求人家收我当学徒,人家看爷爷的面子,把我留了两天,手把手地教我。这些民间高手,不懂什么理论,就只会手把手地教。两天里我就专心看了做,做了看,可事情就蹊跷在这里,看着简单,做着也简单,配料也不稀奇,可你就是做不出来人家的味道。在店里,人家手把手教的时候还差得不太远,离了那个店,我回去后自己又做了两回,简直给人家的味道拾鞋也不配。
他还常带我到深山里,我们看野景、摘野菜、喝野水——也就是泉水。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野菜刚刚开出来,那种味道,干净极了,鲜美极了。那时候的泉水也最好喝,还残存有冰雪的气息,同时也有点儿酒的韵味,杂糅到一起,甘冽凉甜。有时候,爷爷还会带一套最简单的炊具,走累了,他就地就能做出一顿饭来。柴火都是就地取材,烤着温暖的火焰,爷爷就说起了火。他说厨师用火不能叫使火,用火,而叫驭火。火分五种:文火、小火、中火、大火、武火或者旺火。《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说,“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他还给我讲袁枚在《随园食单》里的理论,“熟物之法,最重火候。有须武火者,煎炒是也,火弱则物疲矣。有须文火者,煨煮是也,火猛则物枯矣。有先用武火而后用文火者,收汤之物是也,性急则皮焦而里不熟矣。有愈煮愈嫩者,腰子、鸡蛋之类是也。有略煮即不嫩者,鲜鱼、蚶蛤之类是也。肉起迟则红色变黑,鱼起迟则活肉变死。屡开锅盖,则多沫而少香。火熄再烧,则走油而味失。”他掉着书袋,也不管我能听懂多少。还给我讲老百姓的说法:硬火瓤火。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燃料,比如煤炭、汽油、电、天然气,这些燃料出来的火就是硬火。柴火、木炭、麦秸秆、玉米芯,这些燃料出来的火就是瓤火。硬火可以瞬间导热,适合爆炒。若做温炖熬的东西,火呢越瓤就越好。
我问他:曹植《七步诗》里写,“煮豆燃豆萁”,为啥煮豆要燃豆萁?他笑呵呵地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这太合物性了。他试过,煮豆就得用豆萁最好,煮出来的豆子最香。就像熬玉米粥,最适合的燃料就是玉米芯。
那,炒菠菜可用什么燃料呢?菠菜根儿?
我说的是五谷,小笨蛋!
现在想起来,他那时每天都在教给我东西,可我什么都没学会。我就是享受着他对我的宠溺,无忧无虑,没心没肺。每当爸爸要把我带走时,我不肯,他也就顺着我,说:
再跟我长长,他还小。
再长就荒了。
荒不了。这孩子,根儿正。
您看看他的成绩!
人这一辈子长着呢,不在这个。学问在万物。
十二岁那年,我和小伙伴们打架拌嘴,听到他们骂我,说我命硬,是个克娘*。回家后我问他:是我把妈妈克死的吗?他半晌没言语,后来把我揽在了怀里,说:别听他们胡咧咧。儿生日,母死时。天下的母子都是一样的。我孙子这不是命硬,是命苦。更值得疼。他摸着我的脑袋,粗粝的掌心发出轻柔的嗤嗤声:你要替你娘好好活。
咋算好好活?
不亏人,不亏心。做自己喜欢的事,长大了养活自己。
前一句,我到现在也不怎么明白。后一句当时就挺明白的。我问他:我跟您一样,当厨师中不中?他呵呵笑着,眼睛里闪着暖暖的光,说:咋不中?中。
爸爸却说不中。他说这是低端劳动服务行业,没地位,没前途,爷爷当初选择这个是没办法,我要再选择这个就是没出息。为了这个不中,我跟爸爸一直干仗,干到他死。他对我而言,一直是陌生的。从小陌生到大,从大陌生到死。
他死了,我不能说自己很高兴,却也绝不多难过。在火葬场,我捧着他的骨灰盒,心里憋得满满的,可是一滴泪都没掉。
掉不出来。
这小子多*啊,爹死了,都不哭。
——周围没人说话,可我知道他们心里都在这么说。可我就是哭不出来。哭不出来就哭不出来吧,也不想哭出来给谁看。反正我不是个好儿子,他也不是个好爸爸。尽管他死了,我也还是要这么说。所以我没有多难过。有必要难过吗?所以赵耀这么体贴地把我接到这里,还真是多此一举。不过,来就来呗,反正暂时也没什么事好做,反正那些来路不正的房子都查封了,只剩下了那栋老房子。
老房子绝对不能回去,爸爸就是在那里跳楼的。所以说他真不是个好爸爸呀,死了都不能给我留个清净的地方,让我想起那个老房子就闹心。
对,是闹心,不是伤心。
我不伤心。
6唐珠:你有病啊
住在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在天台上坐到了半夜。浙江有个天台县,县里有个天台山,宋朝的时候我就听说过那个地名,不过那时这个词是属山属水的,怎么会想到有一天这个词会密切到自己身边?在最没有诗情画意的城市楼顶,那一片赤裸裸的水泥地,直面天空,是谓天台。
十一米宽,十二米长,除去楼梯间所占,算起来天台的面积不过一百平。可是在这拥挤的都市,它已经足够安静,足够阔大,足够珍贵。那个夜晚,我在露水的渐渐润泽中,躺在楼板上,仰望着天空。天空上闪烁着可怜的几颗星星。当然,无论看见的星星有几颗甚至一颗都没有,我都知道:星星就在那里。如果换个地方看,比如到内蒙古的某个草原,在新疆的某片戈壁,我就一定能够看到。
——活得越久,不相信的就越多,相信的也越多。因为这些相信和不相信,我就活得越来越从容。能让我慌张的时刻,非常非常少。还会有吗?我简直怀疑。
深夜雨来,隔着窗都能感受到雨声的沉硕。我准备停当,提步上楼。路过二楼时,留神静听了一下,没有任何响动,睡着了吗?真知趣。
推开楼梯间的门,粗直的雨线密密地砸在楼板上,噗噗噗噗。如果是在唐朝乡间的路上,这样的雨线一定能够砸出小小的尘烟。可是这里没有。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楼板,没有尘土,也就没有尘烟。我转到右侧的墙边,楼梯间顶棚的装饰檐很宽,足足留出了一道一米左右的廊。墙上已被我粘好了一排挂钩。当然,在做这一切之前,我早在天台门上装了一把传统的铁锁。这个时刻必须把门锁得牢牢的,任谁也别想打扰。
在廊下站定,我脱掉所有的衣服,连同浴巾一一挂到钉子上。把水桶放在流势凶猛的滴水檐交集处,雨水很快聚集了起来,漫过了桶底。我先把毛巾蘸湿,上下擦拭。很久没有下雨了,这样大的雨,气息有些凉,要慢慢适应一下。忽然想,这个过程,是不是如同做爱之前的预热?呵,因为从没有做过爱,我的思维都很饥渴了吧。
擦过几遍之后,我来到雨里。先是激灵灵地打了几个冷战,便是一阵彻骨的神清气爽。没有闪电,没有打雷,只有雨。这真是再好不过的甘霖之浴。哗哗哗的大雨尽情尽兴地下着,天像漏了一般。雨是云,云是气,气是水,那些水又是从哪里来到了这里,让我有缘沐身其中?据说大脑有很多种喜欢:喜欢色彩,颜色能够帮助它记忆;喜欢气味,薄荷柠檬都能让它保持清醒;喜欢音乐,音乐能有效对它进行调节和放松……我的大脑,它喜欢雨水。不,不仅是大脑,大脑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的身体,我这吞食了珠子的身体,它喜欢雨水——不,不是喜欢,而是需要,且是必需。
呵,在这雨里,我想唱歌了。曾唱过“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唱过“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唱过“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也唱过“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今天晚上,脱口而出的是苏夫子填的《定风波》。这韵位均匀的双调,又名《卷春空》《醉琼枝》,无论哪个名字都合我心。其纡徐为妍,声情迫促,为我深喜,只是许久未唱,生涩许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偶一回眸,赫然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黑黢黢的,寂寞无声,如同*魅。
好吧,我怕。我尖叫起来。一边尖叫一边下意识地护住身体——其实什么也护不住——一边想着该怎么办,那人却已经朝我冲过来,我往最近的南女儿墙那边奔去,这一瞬间已经想好,不行就跳楼。这房子每层高不足三米,这天台总不过八米多高,下面还是松过土的菜园,跳下去应是小劫,料无大碍。
他倒是手疾眼快,闪电一般一把把我抱住。他的喘气声粗壮急促,能听到他的心脏正扑腾扑腾地狂跳。我当然不能束手就擒。一丝不挂地被人抱着,这简直到了失节的边缘不是?只能作困兽斗。我一边拼命撕咬揪扯,一边观察情势。眼看蹭到了南女儿墙边上,跳是不可能了,那就撞墙吧,把头撞破,做寻死状,吓唬他。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亡命之徒的疯狂都很可怕。
你干吗?!他吼。
是他。方才回过神来。这栋房子里,除了他也没别人。
放开!我也吼。
脱离他的怀抱,我三下两下穿上衣服,有什么穿真是好啊,此时的衣服仿佛铜盔铁甲,我顿时觉得安全无比。
喂,你怎么回事?
不应答他。只是有一点也让我好奇:你怎么上来的?
你怎么上来的我就怎么上来的。
我明白了。他先上来的。上来后他就待在了楼梯间的左侧,雨声又大,所以他没听见我上来。算是各吓一跳,扯平了。
他拉住我的手,奔向楼梯间的门,想要拉开,却是徒然。锁着呢。我说。我拿出钥匙,打开锁,做了个请君滚蛋的手势。你,还要在这里吗?他讶异极了。我点头。等一场这么大的雨容易吗?喂,你这个人!暗夜的雨光中,他喊:你有病啊?我再点头:对。
重新锁好门,又把整个天台查看了一遍,我脱光衣服,再次回到雨里,雨却好像被惊没了似的,越下越小,终于停止。我擦干,穿好衣服。两只桶里的雨水几乎都快接满了,一次拿不下,只好先拿一只。还好,这次的雨量够我一周之内再擦洗一次。
三楼通往天台的楼梯拐角处,金泽赫然在那里坐着,仍是一身湿衣。看见我,他慢慢地站起来。木木的、呆呆的,有点儿睡眼惺忪待要醒又醒不过来的样子。
我怕再有别人上来。他说。这个人情还是要承的,虽然无效。我点头致谢。他指指我手里的桶:这水留着干什么?我说有用。怎么用?老脏脏呢。他说。
“老脏脏”,这童稚的句式有点儿熟悉,似乎在哪里听到过。我想笑,却强忍住。我说这是我的事。他抿抿嘴唇:好吧。随便你。我说今天这事,你肯定不会对别人说,对吧?这个嘛,是我的事。他阴阳怪气。我说以你的身份,去说一个用人的闲话,不会这么掉份儿吧。他说和掉份儿不掉份儿没关系,主要是我没有这个恶俗嗜好。
小小的沉默。
你,真的有病?他又问。
喜欢淋雨而已。
这就是有病。
那你上天台干什么?是不是也是淋雨?也是有病?
我那是……跟你不一样。
肯定也是有病。
应该是击中了他的七寸,他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方又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唐珠。
是不是“极致”那个——思乐泮水?
对。难为他记性这么好。
你哪一年生的?哪里人?爸妈做什么的?他问。
你哪一年生的?哪里人?爸妈做什么的?我也问。
他愣在那里,没有回答。当然我也不需要他回答。这种反问只是一种抗议,不需要答案。
回到卧室,我砰地关上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乍想是有些奇怪,今天这件事情,我对他居然是如此不客气,不客气得近乎亲昵。我不过是女佣,他到底是客人,这不合常理。可是再一想,这也合我的常理。经验告诉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要明明白白地在彼此之间划清楚界线,立好规矩。得罪了他也无所谓,大不了一走了之。活了一千多年,跳了那么多次槽,还怕再多这一次吗?
这件事情也让我有了个基本判断:这个金泽,他起码不是一个坏人。当然也不能就此说他是个好人。不过无论好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别打扰我,让我安安静静地把日子过下去。
7唐珠:安胃
一个人孤身在世,一直一直活着,活到周围没有一个亲人,这是什么感觉呢?——镜子的感觉。
我看着镜子。每天晚上,我都会久久地看着镜子。鉴,这是镜子最早的名字吧。比我更古的古人以水照影,称盛水的铜器为鉴,鉴就成了最早的镜名。汉代的时候有了铜镜,鉴也渐渐被称为镜。而到了唐朝,《旧唐书·魏徵传》有段话人人皆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能拿镜子来打比喻,可知此物已经成为家常。
葡萄镜、花鸟镜、盘龙镜、双鱼镜、八卦镜、圆镜、葵花镜、菱花镜,镏金错银镜、贴金贴银镜、螺钿镜直至如今的水银玻璃镜……一千四百多年来,我不知道照过多少面镜子。尽管我每过两百年就给自己加一岁,现在已经号称二十一岁,但是毫无疑问,无论照多少面镜子,这张脸似乎永远都是当时十四岁的相貌:圆脸平眉,耳厚唇丰,额头高亮,下巴饱满。
镜子里的人,就是我。这个世间,只剩下我。每当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这么想。父母的容颜早已经模糊,我要常常照着镜子,看着自己,才能依稀想起他们的模样。无论如何,我总该有些像他们的吧?或者,作为女子,我应该更像母亲。母亲仿佛比我漂亮,比我高,比我白,我似乎什么都不如她,除了才学。
论起来,我是该比她有才学。颠沛流离中,我走遍了中国的所有土地,不,也许应该说,我走过的版图面积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得多。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中国的面积多了又少,少了又多,从西域到东海,从南疆到北国,我辗转流荡,吃过各种各样的食物,穿过各种各样的衣服,住过各种各样的房子,走过各种各样的道路……因受“封建礼教的严重迫害”,清朝之前的女子最重要、最主流、最正当的事情就是嫁人,除此之外的选择实在有限。因为不能嫁人,我便让自己在这有限里做到极限。剪云镂月,做过绣女;炮凤烹龙,当过厨娘;能弹会唱,习过艺伎;在一个医生家当帮佣时顺便还学了一些医术……起初学东西的时候,我很努力。后来慢慢淡下来。在这世上,想要万寿,就不能成名成家,就只能做个平凡的人,淹没在人海里。既然要淹没在人海里,有的没的学那么多做那么好干什么呢?学得再多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让那些不能万寿的学吧做吧,让他们成名成家吧。
我只要万寿。
虽不再努力致学,但慢慢经见着世间之事,三十六行即使不能全知,却也都能算得上半解。而于人前,我通常只是一副未解的样子。在女子职业空前多样化的当今,也只选择最无奇的行当,免得麻烦,比如帮佣。粗算起来,我在各种各样的人家里当过少说五六十次丫头。最近一次是在六十年多前,上海,一个国民**官家。那一天,他和太太慌慌张张地收拾了金银细软,说要出趟远门,嘱咐我好好守家——后来我知道他们去了台湾。我一直给他们守到了上海解放,守到解放*把他们的宅院接管走,然后,我就成了“劳动人民”。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就没有再给人当过丫头。先是有很长时间不允许请用人,再有钱的人家也不行,说这是剥削。从唐朝以来,再没有这么长时间,家家户户不请用人。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最起码对我而言,当用人真是一个上上之选。原因很简单:东家日子不错才会雇得起用人,用人不用为自己基本的生活资料操心。至于受委屈嘛,生而为人,在哪儿能不受一点儿委屈呢?而比起江湖上五行八作的老板,一个好东家给你的委屈一定是少之又少的。原因也很简单:用人适应东家、东家调教用人,这都需要费时费力,智商和情商成本均不低,因此一旦确定了信任关系,若无太大意外便不宜破坏,我尽可以数载之内稳定无虞,安心吃饭。
说来好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我相同,这世间很多事情于我而言都失去了新鲜感,对吃却依然兴致如初,基本到了“上不吃天,下不吃地,中不吃空气;死的好吃,活的好吃,死活都好吃”的境地。为何如此?想了很久我才有些明白:人生大事无非饮食男女,男女份儿上既是无缘,那饮食就成了特别重要的福利。最起码每天早晚的粥的稀稠冷热都不一样吧,每天每顿的菜的酸甜咸辣都不一样吧,百种千样的它们每天都会妥妥帖帖地进到我的肠胃里交融沉淀,和我的血肉亲密接触,给我欢愉,让我踏实。而让我惊叹了又惊叹的就是: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好吃的食物啊,来安慰我千年的身体和千年的心。
这么多年来,所谓安慰,在我的词典里一直是“安胃”。
没吃的我会饿死吗?好像不会。挨过很多次饿,我都没有死掉。最近一次挨饿是在半个世纪前,年深冬,那种感觉……太难受了,还是打住。
8赵耀:被她打了脸
喂?
喂。
金泽呢?
一早就出门了。
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
怎么又是不知道?
我不好问客人这么细吧。
我一会儿到。
好。
她自然是不知道。
她不知道的事,其实我知道。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常听女人们这么骂。男人是东西吗?要是男人是东西,女人也是东西。
女人这种东西,有意思起来,也是真有意思。
既然是直男,就总得有女人。当货车司机的第二年,我十九岁吧,在一个路边店,被老板娘给破了童子身。她只要了二十块钱,要说真不贵,她人也周到,活儿也好。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吃了亏似的。后来想想,可能是觉得该配个处女,呵呵。
之后就是一路野花野草。“十个司机九个嫖,还有一个在治疗。”只要有点儿钱,解决基本的生理问题就不是个事儿。直到进土地局开车,有了单位。一旦有了单位,就不好随心顺意地胡来了,作为一个有单位的人,且是一个懂规矩又守规矩的人,你就得拘着规矩。不拘着能行吗?你不是你,你的脑门子上贴着单位,你的脊梁后面站着领导啊。
既然拘着了规矩,也就想按照规矩成个家。可是这个念头动了一下就灭了,知道不现实。自己眼界挺高,能看入眼的女孩子都不错,追求呀表白呀这类的酸事儿也没少做,有几个甚至都到了打情骂俏谈恋爱的地步,末了还是有花无果。一句话到底:没钱没权没势,谁跟你呀!
那就单着吧,不急。到了现在,什么都有了,经手的女人越来越多,就更不急了。结婚这事是正经事,就得找个靠得住的。怎么叫靠得住呢?外貌总得周周正正,身体总得皮皮实实。心性呢?说了归齐,最重要的一点儿,就是得懂事儿。一个女人要是懂事儿,就一定脾气好,就一定够聪明,就一定好相处。那能省多少心啊。
唐珠这丫头看着倒像是个懂事儿的。不多说也不少说,说出来的话从不掉板。不多干也不少干,交代她干的事都很妥当。既不愚笨,又守本分。不见嗔喜,平和稳重。以她这个年纪,能拿捏出这么好的劲儿,配得起我给她的这份儿工资。不过她在我这里也算是一份美差吧,这种待遇,这种工作量,别处肯定是不好找,她应该是挺珍惜的。
——看着像个懂事儿的,也只是看着像。到底懂不懂事,谁知道呢?懂事儿懂事儿,总得经事儿才能知道。有多少看着懂事儿的人,一经事儿就现了原形。
且先试试。
唐珠正在客厅打扫卫生,我冲她笑笑,直奔二楼,进了金泽的房间。翻衣柜,翻行李箱,翻抽屉,最后翻的是纸箱,箱子正口的地方还用透明胶布牢牢地封着,只好去开箱底儿。手劲儿有点儿猛,哗啦一声,东西摔了一地。都是一些家常零碎:毛绒玩具,*棋象棋,乒乓球拍,几本影集,一个相框,相框里装着老照片……没有我要的那个东西。
也是,那个东西哪能这么容易就现形呢?
过来帮个忙。我打开门喊。唐珠很快上来,等着我的意思。看见这情形,她也就明白了,利落地把地上的东西捡到箱子里,把箱子底儿扣好,开始清扫地板。我下楼,在客厅里边喝茶边等着她终于忙完,坐在我的对面。
唐,珠……嗯,你这名字真不错。这么取名字有什么讲究吗?我没话找话。
我们兄妹四个,分别叫珍珠宝贝。可能是我爸妈穷疯了吧。
这回答我很满意。有点儿幽默,还提到了穷。
我是来看看金泽缺不缺什么东西。他只说他不缺,我不大信。我笑:他,怎么样?
您指的,是什么怎么样?
我便细细问,吃饭怎样?睡觉怎样?哭过没?笑过没?看不看电视?打电话多吗?有没有人来看他?
她只答吃饭,说其他的都不清楚。
你还是要多费心。我不能常过来,常过来呢,以他的性情,他也不自在。所以你就是我的帮手,要替我周全照顾。不会让你白辛苦的。我长叹口气,说金泽也不容易,如今正在坎儿上。
他,有什么事吗?
我又叹口气,给她叹出一本故事:金泽的爷爷做饭手艺不错,是个好厨师。金泽母亲生金泽时难产,儿生母亡。此时爷爷刚刚退休,便把孙子带回了老家。隔辈亲是铁律,爷爷把孙子惯得一身毛病,不过爷孙两个倒也其乐融融。金泽直到十五岁那年爷爷去世才来郑州跟着父亲生活。“金局”,我这么称呼金泽父亲,说十来年前我正给金局当司机,金局在重要部门当得好领导,却领导不好正在青春期的叛逆儿子,父子两个争端频起,对抗渐烈,到后来几乎不能正常说一句话。金泽高中勉强毕业后又自己报了烹饪学校,把金局气得半死,几乎是派人押解着送他去了法国读书,想着花大价钱起码能混个外国大学文凭,孰料他到法国没多长时间便自作主张去上蓝带学校,金局立马断了他的财路又把他逼回国,父子两个对峙升级至最高峰,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金局无奈,索性对金泽放任自流,随他晃荡,直到前些天自杀才算了结这段父子孽缘。
自杀?小丫头惊诧了。
抑郁症好几年了。还有,早就传出风声,说上面要查他。这种事情一般没有空穴来风的。今天,是他百日。
她垂下眼睛。心软了吗?我说金局去世前跟我托付过好几次,说自己万一有了什么,让我念着旧情帮他照顾照顾孩子。我自然也是劝了又劝,想着他不会较真儿去死。可是这世上的事,谁想得到呢?至于金泽,他就是不托付我也会照顾的。我比金泽大十岁,一直觉得他就是我的小老弟。怎么会干看着呢?金局人已经过世,虽然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可是非法所得还是要追缴的,所以金泽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多年前金局分配的一套福利房。那套老房子多年不住人,还是顶楼,夏天热冬天冷,没法子住。前些天我把那房子给装修了一下,又添置了些新东西,算是像个样儿了。就是得跑跑味儿,所以我把金泽安顿在了这里……我顿了顿,观察着她的神情:
金局就是在那里了结的。在那里的天台。
哦。她垂下眼睛。眼圈红了吗?是感慨于金泽的辛酸家世还是感动于我的高尚品德?毕竟世事凉薄,十来年前的司机还能在旧主遭难之际对他的亲人慷慨出手,我这也算是情义犹存道义温暖吧。
是时候进正题了。我说你觉得奇怪吗?刚才我在金泽的房间里找东西。她不答,只是看着我,等着我说。我干咳了一声,说:我是在找东西。她说:哦。这么一个感叹词后,还只是看着我。我只好接着说:金局去世前告诉我,他的东西里,有一样是金泽不该看到的,要是他看到了会对他非常不好。他要我找到,处理好。这事对我是无所谓,我主要是受金局之托,为了金泽好。
哦。
可是你看,我不大方便。诚恳柔软的语气:你能帮帮我吗?也是帮他。
金局,他为什么不把那个东西事先处理好?
这个么,我也不清楚。应该是想处理的,可能是自己也记不得放在哪里了吧。
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文件。我淡淡:内容嘛,我不知道。你也不必知道。
我压根儿没兴趣知道。她也冷着脸,样子还挺酷。
看得出你是个可靠的人,所以拜托你也最放心。我停顿了片刻,继续说:文件可以放在U盘里,可以放在移动硬盘里,可以存在手机里,也可以存在笔记本电脑里。金泽的手机我已经查过了,没有。电脑硬盘和移动硬盘也全部拷贝查过了,也没有。
她没说话。
我想,很大的可能性是U盘,U盘很小,不易察觉,可能金局会把它无意中塞在了哪个缝隙里,事情的麻烦之处也在这儿。怎么样,能帮忙吗?我故意不看她,免得她不好意思:等麻烦解决完了,我给你发奖金。
她保持沉默。是在琢磨奖金数吗?
不会亏待你的。一定是大红包。先给你一万,怎么样?我说。
抱歉,她终于开了玉口:我不偷东西。
偷?啧啧。被她打了脸,用这么狠的一个字。可一时间我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把握自己的表情。不能恼,也不能笑。
但也不能这么僵着。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得,当我没说,我自己来。请你保持沉默,免得金泽误会。明白吗?
她点点头,起身去了厨房。
这么好的挣钱机会她竟然放弃,还不怕得罪我这个东家,看来这个姑娘挺任性,不懂事儿。也是我想得有点儿简单了。小门小户出身的孩子,也不能一律小看,她或许真有什么大气性?
我不舒服,很不舒服。可是,有点儿奇怪的是,不舒服的同时,又有点儿舒服。像按摩。按的时候又疼又麻,按完了倒有点儿觉得浑身通泰。她现在中立着,不偏不倚,这让我放心。最起码证明了她有主意,不浮躁,不会被钱一拳打倒。也意味着将来一旦站到我这边,就会比较可靠。
以后要慢慢地在她身上下点儿功夫。她值得。可今天这事儿也不能就这么了了,我得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9唐珠:雪亮的钝刀
终于明白了那个大雨之夜金泽为什么会在天台,也终于明白了赵耀的目的。
当我活得足够久,当我看到一个又一个人在我眼前十年二十年老去,当婴儿变成少年,少年变成青年,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或者某些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没有征兆地死去,变成骨灰,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人”的过程。“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日光之下,也并无新鲜之人。人事人事,所有的事都在人的身上路过、体现、沉淀和爆发着,说到底,事的根基还在于人。唐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很多人只是身份不同穿衣不同语言不同,他们制造的那些事只是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外壳不同,但是,本质却是相同。如果说世相的外在是流星赶月风驰电掣,那么人的本质就是在原地打转,甚至是把原地踩成了一个越来越深的坑。
在人间,没有神。所谓的神话,水落石出之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赵耀善待金泽这貌似的神话,很容易就露出了笑话的马脚。“他,怎么样?”这口气听着是在关切他的朋友,但必然不会这么简单。关切是不必拐弯来问我的,直接问金泽岂不是最好。既然拐弯来问我,必然有这么问的用意。还有,缺不缺东西的话虽是贴心,我却也不大信。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种在心里,让我觉得好像哪里有一点儿不太对劲儿。纵是最不谙世事的傻丫头,我从唐朝活到现在,哪怕十年多一个心眼儿呢,也该有一百多个了吧。虽然一般情况下我只用一个,不过在适当时候,那些多出来的心眼子也会自动开开窗透透气儿。
因此,等到他说到“这事对我是无所谓”,那一点儿不大对劲儿的感觉终于落地生根,茁壮成长:金泽,这个落魄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离他十万八千里,唯有赵耀暖他于酷寒之中,管吃管住管伺候,又尽心竭力地要替他的父亲清除一件有可能伤害到他的遗物。有这么好的人吗?有这么好的事吗?好至于此?我便可以确定,一定是大有所谓。而“为了某某好”,基本上都只是为自己好。如无特例,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赵耀对金泽所做的一切,终极目的只是为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才这么处心积虑地来找它,还要亲自来找。而诚如他所判,在这件事上,相比于其他任何人,我是最适合的助力者。
当然不能帮他的忙。当然要拒绝。
但我会保持沉默。
经历了这么多事,我发现自己最会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沉默。没办法,沉默常常是最好的选择。是隐忍,是中立,是观望,是底线,是智慧,是狡黠,是抗议,是妥协,是接受,是婉拒,是肯定,是否认,是犹豫,是笃定……可以是一切,也可以不是一切。因为涵盖了所有的方向,因此沉默总是对的。
所以,我只沉默。任他去吧。金泽,说到底,他关我什么事呢?再说到底,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关我什么事呢?别人都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唯有我,是那万里无云万里天。
打了个寒噤。突然觉得冷。人在世上练,如同刀在石上磨。因为练了太久,我已经把自己练成了一把雪亮的钝刀。钝是刀鞘的表情,雪亮是刀刃的锋利。锋利也是虚拟的锋利,其实也没杀过人,至多只是在第一时间里洞悉,然后用刀鞘来保护自己。
要想活得长,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别人伤害我。不让别人伤害我的最重要前提就是不去惹事儿。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察言观色,谨小慎微,按照每个人的喜好留神收声,循规蹈矩。惹不起的人坚决去躲,躲不起的人坚决要逃,逃不脱的人坚决能忍,不好处的人坚决不处,好处的人也坚决不长处。处得再好又如何?好得再久又如何?一二十年过去,他们容颜大易,老态日显,甚或鸡皮鹤发,“发短愁催白,衰颜借酒红。”而我依然唇红齿白亭亭玉立,成为一个例外,我和他们怎么面对?我怎么对他们解释?难道说我整天整容?
——多年来,我之所以一直到处流转,漂若浮萍,一是容颜不老让人生疑,二是为了不至于和人太过深情地结交。若是结交得太深,一旦到了不得不永诀的时候,就会伤心。
不想伤心。
脚步声响,赵耀跟过来了。是要补台吗?
你别想太多。其实找东西的事,也不多要紧。倒是另有一件事,还想请你帮忙。之所以安排他在这儿待一段,我的主要目是想让他缓一缓。不过他到底是这么大的人了,总窝着也不合适,得多出去走走,找个工作什么的,先让心情秩序恢复正常。就是不找工作,出去会会朋友也行,挣钱不挣钱的倒在其次,反正我会保证他的卡上有足够的零花。可是让他出去这话我不能说。不能显得人家没了父亲,就得我来管教似的。要是你们投缘,能多说上几句话,你就开解开解他,假装不知情劝他几句,说不定他还能听进去。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怎么样?这个忙能帮吗?要是能劝他多出出门,我也给你发奖金。
大红包?
大红包。
好啊。
*昏时分,金泽回来,进门就上楼,说不吃饭。想到今天这个日子,不吃便不吃吧,我只给他泡了一壶玫瑰花茶送了上去。他在屋里一直闷到第二天晚饭时分才下来。那天晚饭我做的是最简单的两菜一汤。菜都是素菜,锅塌豆腐、清炒西兰花。粥是百合粥,另有一道红枣甘草汤一碗蒸蛋。手工蒸的白馒头。
这个很不错。温水调的吧?他吃了一口蒸蛋,问。
对。
什么道理?
不知道。只记得老话说的,温水调鸡蛋,凉水蒸馒头。
他倒是知道。他说水过凉或者过热,调出的鸡蛋便又碎又澥,还不好消化。热水蒸馒头,内外气压不均衡,馒头皮容易裂开……不知不觉,水话聊开。吃了一千多年的饭,喝了一千多年的水,在这个话题上,他自然跟我不能比。炖河鱼适合用凉水,炖海鱼最好用热水。因为河鱼骨头软,好炖,海鱼骨头硬,得用热水把它泡酥。蒸饭一定要用河水,因为河水照到的阳光比井水多,蕴含的太阳真气自然也多。造酒呢最好就用泉水,因为泉水比较甘甜,造出来的酒也甘甜,但是切忌使用那种流得太急的泉水,否则造出来的酒不醇。雨水冲茶?当然也是可以的。古人都这么做,因为雨水轻浮——轻浮在此是个好词。但是不会用暴雨的水,因为蕴含的戾气太多,冲出来的茶会很有杀气。对了,清明节、中元节和寒衣节的雨水也不能用,阴气太重……这个年头,除了养生专家,想碰到个对水性有兴致的人聊聊,也还真不太容易。
突然发觉自己的话似乎过量,连忙打住,收拾碗筷。
你知道的,还真多。
女人是水做的嘛。我打哈哈,话锋一转:你就这么整天宅着吗?怎么不找工作?
我工资太高,没人出得起。他冷下脸。
哦?你会做什么?
什么都不会。他看着我,有点儿挑衅。
要是什么都不会那就去学。你这么小,学什么都来得及。最起码给自己挣口饭吃。
你什么意思?有什么资格来训导我?谁授意的?赵耀吗?
这家伙,简直是秒变刺猬。
只是说句实话,没什么意思。我有什么资格来代表东家?不过和你一样,寄人篱下而已。好在咱们还是略有不同,我有工资。
他煞白着脸,起身上楼。第二天开始便频频出门。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看情形应该是在找工作,因他偶尔会带几张招聘启事回来,和别人的通话问答中也透露着这方面的迹象:房地产、证券、电子商务……左不过是这热门的几样,却仿佛左左右右都不中他的意。倒也总是照着钟点回来,一日三餐必吃。我也更认真地做,无非是家常饭,只是更精心。醋椒土豆丝、凉拌三片、油焖笋、锦绣卷、尖椒牛柳、凉拌茭白、红烧肉、排骨莲藕汤、苦瓜鲫鱼汤、绿豆小米粥、玉米粥、千层饼、牛奶馒头……一个大男人,若要认真吃起饭来,那还是值得一做的。而且看他吃的劲头,似乎也并不嫌弃我的手艺。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hef.com/bhpz/915.html
- 上一篇文章: 味甘平,补中益气,百合不仅好吃,用处大大
- 下一篇文章: 中国唯一的甜百合,养肺润燥,还能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