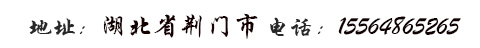流泪谷中的百合花卅四
|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野地山谷里的百合,完全是神自己在撒种、浇灌、伺弄,却活得争奇斗艳!人用自己的办法精心伺弄家养百合花,却看上去这花朵一天不如一天。神既然如此全能,可是人类却常常不愿意来倚靠他,真是可惜...... 二 我们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在东关教会时就已经被日本*队和皇协*劫掠一空了,一家三口几乎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北散湖村。 我们刚在尚青梅弟兄的家里安顿下来,北散湖和附近村里那些我曾教过的学生听说相忱和我来了,马上都赶到尚家来看望我们。孩子们看见我们缺少日用品,就纷纷从各自家里为我们送来被褥、衣服、鞋子还有食物等等,有家境稍好的学生甚至给我拿来了肥皂。感谢神,我们一家人的缺乏就是这样在弟兄姊妹的爱心中,顷刻间成为丰富并且有余。夜晚,我躺在孩子们送来的被褥当中,虽然这些被褥和衣物都是农村家纺的粗布做成的,但她们让我感觉到格外的厚实,格外的温暖。 尚家的生活比较富裕,有属于自己的场院和石磨,有小牲口,还有自己家的粮囤,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尚青梅夫妇俩和三个儿子都信主,而且都是热心事奉,父亲尚青梅和小儿子尚志荣都是传道人,平时家里的生活主要都是靠尚青梅的大儿子在田间耕种劳作来维持。初到尚家的那几天,尚老弟兄热情地坚持要我们和他家人一起吃饭,但是相忱和我都觉得不应该这样麻烦人家,相忱就对尚老弟兄说“我们长期在这里住着,我们还是自己开伙吧。”尚老弟兄推让再三,也只好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熬小米粥,蒸窝头,也自己腌酸白菜。 窝头不像馒头那样容易蒸熟,因此需要在底下做一个拇指大小的孔洞,这样蒸汽从内外同时蒸才更容易熟。我从前在东关教会伙房里向张大妈学得的技艺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在一个瓦盆里用水和好玉米面,然活捞起一个面团托在左手的掌心里,右手的拇指从侧面插入面团中间,接下来左手在外面托着面团一边颠着一边转着右手随着面团的转动在里面不住地按压出一个洞,最后把有空洞的一边朝下放在蒸锅的屉上,再蒸熟就算完成了。相忱并不知道我早就学会了怎样蒸窝头,从外边回来一眼看见桌上的这盆窝头还以为是哪位乡亲送来的,就略带惊喜地问我.:“这窝头是人家送给你的?”听他这样说,我强忍住心里的兴奋,微笑着一字一句地对相忱宣布,说:“是…我…自…己…蒸…的!”“你会蒸窝头啦!”这下相忱吃惊得几乎叫了出来,两眼瞪着面前的这些窝头,就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见窝头似的。吃饭时,相忱一边嚼着我做的窝头,一边对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能来和我一起吃这个。我明白相忱此时并不是在简单地夸赞我,他实在是在赞美神所成就的这一切的奇妙作为,我也愿意和他一起将这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愿意作主手中卑微无用的使女。 虽然我们自己开伙做饭,但是生活需用的口粮主要都还是由尚青梅弟兄为我们预备,另外村里的乡亲和我的学生也常送些粮食和蔬菜给我。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艰苦状况是今天的人所不知道的,即使如尚家这样的殷实人家也不是一年到底都能吃到玉米面的,可是给我们的供应却没有轻忽过。 与父亲和弟弟相比,尚志荣的大哥显得质朴少言,但村里的人一致都说他真是个“好信主的”。因为在当时小米稀饭是比较好的饭食,所以尚大哥常在吃饭时为我们端来二盆自己熬好的粘粘的小米稀饭,或是两块热气腾腾的红薯,进来一声不响地放在桌子上,出去时再顺手打开盖子看看我们缸里腊的酸白菜还有多少,如果少了就从自家拿一些来加在里面。我们日常的饭食中仍是小米稀饭或玉米面粥,窝头除了玉米面的以外,还有高梁米面和掺榆荚的。榆荚窝头就是像菜窝头一样,只是用榆英来代替了菜,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窝头上锅蒸。因为榆英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很好吃,所以这种榆英窝头就是我最喜欢的。做窝头用的玉米面也经常需要我自己拿着玉米到村里公用的石磨上去加工,磨好了再用一个大号的竹箩把其中的糠皮筛出去。石磨很重,我不得不用腹部顶住辘轳上那个胳膊粗的木柄,上身尽力向前探出去,靠着全身的力量推起石磨向前走。村里有的姊妹看我推得实在太吃力,就提醒我说:“你可以去村里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借一头小驴来推磨呀。”可我觉得还是自己推比较好,所以仍旧还是自己推。相忱在家时也会来帮我,要和我轮换着推,说:“我推点吧,你歇会儿。”但我却舍不得让他上手,只叫他抱着孩子坐在一边看着。相忱虽是常在外奔波劳碌,但他的饭量还是和从前差不多,身体也一直很硬朗,只是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瘦。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这时的饭量却比以前大了很多,一顿饭能吃下一碗稀饭和两个窝头,以后都再没有吃过那么多的时候。要自己开伙做饭就还得有烧的,这又开始令我犯难了。离成安县百多里外就有一个大煤矿,煤在当地人家的日常生活中只是一种很平常的东西,乡村里人都是去外边买来煤面,自己打成煤饼作为烧饭和取暖的燃料,可是我们哪里有钱买煤呀?我不愿意因此事拖累弟兄女姐妹,就私下向老乡打听,说:“我没有烧的,我该烧什么呀?”有的老乡教我说:“早晨四五点钟,你去地里割高粱叶,回来晾干了就能烧。”高粱的叶子可以用来烧火,但是只有在每天的凌晨时分,被夜间的露水所充分浸润的高粱叶才能割得下来,等到太阳一出来,被晒干的高粱叶就硬翘翘的割不动了, 清晨四五点钟,我就起身离家,独自一人走在村外田间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天与地之间仍然被充斥的黑暗所阻断,然而我却望见前面最遥远的地方正有一道光显明出来,把天地重新拉近,再拉近…… 下到地里我才发现原来高粱真的很高,高粱叶包着高粱秤向上一直长到顶上,我必须尽力垫起脚才有可能很勉强地够得到最上面的叶子。我伸手把高粱叶从顶上直捋到底下,使劲地撕扯下来放在一边,再接着去捋旁边的那一棵,等到差不多够数了,就把刚刚捋下来的那些叶子从地中间抱到田埂上,码放成为一摞,用从家里带来的那根拇指粗的麻绳从中间拦腰捆住,再用力扎紧,背回村里去。宽长的叶子包着茎秆密密实实地向上长,就像一个个矗立在地上的巨大的高脚杯,整整一个夜晚的露水都会顺着叶片汇聚到和秆的交接处。当把叶子往下捋的当口,里面盛满的露水就哗哗啦啦地洒落在我的头上、脸上和身上,这一捆叶子捋完了,我已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从头到脚全都湿透了。 每一个清晨都要这样为当天预备所用的燃料,村子近处地里的高粱叶渐渐地被捋完了,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路也随着时间向前方延伸,最后甚至要到离村四五里以外的地里才能找到可以采摘的高粱叶。在弥漫着灰暗的大平原上,极尽四顾之内似乎每一天就只有我一个人来来往往,但我确实看见有一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主正在天边的那一线光明中与我同在,他不仅注视我,也用大能的手臂帮助我,如果去时空手还算作轻松的话,那么回来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湿漉漉的高粱叶压在同样湿漉漉的身体上,步子越迈越小,前面的路却仿佛是越走越远……怎么还没有到家啊!那捆背在我身上的高粱叶也像是越来越重了,正把我的力量从身体中间一点一滴地挤压出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主真的帮助了我,因为我真的相信我手所能做的并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我的主;我肩所能担的更不是依靠我,而是依靠我的主!我一切手所做成的,肩所担起的,都是主所为我成就的恩典! 待到了秋后,“麦茬”就是小麦收割过后留在土里的残根成为另一种可供我使用的燃料。我身后背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大筐子,用手里拿着的靶子把麦茬从干硬的土壤里一个一个地扒拉出来,捡起来,抖落掉上面带的土坷垃,扔进背上的筐子里。虽说高粱叶和麦茬都是可烧的,却实在是很不经烧的,日常做饭需要很大的数量才能将将够用,这样我几乎天天都不得不出去捋高粱叶或是拾麦茬。偶尔有个机会和村里的姊妹们一起到附近的碳场去捡拾一点点人家选碳剩下不要的“碳末”,回家来加上点水,在一个用三块砖头围出来的简易的“模子”里做成湿“煤饼”,放在高粱叶上一起烧。 农村里“住的”和“吃的”一样艰苦。来到北散湖以后,尚青梅弟兄安排我们住在他家的两间西房里,一明一暗的里外间,每间各有大约十平方米上下,外边还另外有一间灶房。房子只有从底下起的那一米左右是由青砖砌成的,再往上直到房顶就都是由碎草秸和*土混合在一起打制成的土坯砖了。尚家院子里的房子都是这样的,这已经是村里最为像样的住房了。 屋子里只有炕边上的那一小块地面铺了一些砖头,其他的都是夯实了的*土地,平时倒也看不出什么分别,可要是不小心撒上点水就难免一片泥泞了。 乡下连个像样的油灯都没有,我就学着别人家的样子,先在一个粗瓷的小碟子里放上一些灯油,然后搓一个棉线放在里面当作灯芯。因为河北省的南部盛产棉花,所以这里用的灯油都是从棉花籽里榨取出来的,这种油灯的光亮特别小,即使点着灯屋子里也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字,而且棉花籽的油烟尤其的大,燃烧时总是冒着黑乎乎的烟,到处都弥漫着那么一股呛人的烟味。 像这样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已经是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可就在转过年(一九四二年)的三月二十日,当时我又一次怀孕已经七个多月了,那天我一口气连着洗了四条被单,这些土布做的被单经水浸湿以后越发的厚重,不成想在我挺直身子,举起被单正往那条高高的晾衣绳上挂去的一刻,竟然动了胎气,我意外地在这时早产了。 一切都来不及准备了,临时为我接生的是住在尚家东边院子里一位被称为薄三奶奶的老姊妹,她也是一位爱主爱人的敬虔人,已经寡居多年,平时一贯很照顾我。我被送进薄三奶奶的院子,这里除了她一个人独住以外没有其他的人。在薄三奶奶的屋里,按照当地的一种说不清由来的怪异习俗,我被安排不是在床上而是直接在土地上生产身子下面铺垫了几层粗糙的*草纸,但我已然无力顾及这些了。可能是因为不足月的缘故,所以胎位不正,孩子的腰先出来了,只好又推回去……村里的姊妹们知道消息都来在我身边和薄三奶奶一起为我和孩子迫切地祷告。在生下这个孩子之前,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地上已经躺了很久很久,并且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平安中心里就没有一丝的惊慌和惧怕,我没有感到异常的痛楚,也没有异常的出血,因为神按照他怜悯的应许在生产的事上赐福与我!(提前2:15) 我生下一个女儿,这是神赐给相忱和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我们俩的第一个女儿。相忱为孩子起名叫袁安湖,“安湖”两个字分别取自成安县和北散湖村这两个地名,以此记念这个我们曾经事奉神的工场,也记念这里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们曾在主里面给予我们的真诚厚爱。直到过去了许多年,每当再提起女儿的名字,相忱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讲述起神在那个岁月里给我们留下的见证。 孩子平安地生下来了,可毕竟是七个月的早产儿,体重还不到四斤,要是医院的育儿箱里放上几个月,可那时我却什么也没有,惟有把孩子放在主温暖慈爱的怀抱中。安湖刚出生时连喝奶都不会,我就只好做面糊糊一点一点地喂给她,神真是怜悯我们,这段时间虽然孩子不能吃,我的奶水却丰富如常,正好村里有位缺奶的产妇,我就叫人把她的孩子抱过来给我帮她喂奶,一直过了四个月以后安湖才开始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的吃奶。好在除了瘦以外,这孩子竟然从来没有生过什么病,唯一让我操心的就是她不好好吃东西,一看见吃的就哭,每次只能让我勉强地用调羹喂上几勺奶,就哭闹着无论怎么哄都不肯再多吃一口了。我们俩当时谁都不懂得坐月子的重要性,我不懂,相忱就更是不懂,相忱的精力都放在主的事工上,我也根本顾不上心疼自己,都是出于神的保守与眷顾,我的身体很快就完全地恢复了。 虽然在这里的生活条件和遭遇到的意外困难,与三年前我在北平生第一个孩子福音的时候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但是惟一没有改变的是神的恩典,即使环境有着诸般变化,我的心里也满有真实的平安。同时,弟兄姊妹们在主里的爱心也给我莫大的安慰和帮助;离开东关教会进入乡村以后,作为传道人的相忱再没有了任何稳定的供应,完全是弟兄姊妹在艰苦穷乏中供应我们一家人的日用饮食。安湖出生后,相忱都没有力量为我们母女预备什么,是乡亲们各家凑一盆鸡蛋还有不多的一点红糖送给我们。我在学校教过的那个叫袁温的男孩子,从他母亲那里要了家里仅有的三个鸡蛋,步行十多里路送到北散湖给我。袁温弟兄今天依然健在,还住在成安县,也已经是八十一多岁的老人了,再讲到当年这件事情,他就笑呵呵地伸出三个手指说:“那时老师生小孩,我送给她三个鸡蛋!” 我自己已经和这里的乡亲们完全地打成一片,我和她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食;我们一起聚会,敬拜;一起祷告,唱诗;也一起去到田间做工。一到棉花丰收的季节,全村能劳动的妇女们都要下地去摘棉花,姊妹们经过我的门口时就会大声地叫我“袁老师,一起去摘棉花呀!”我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和她们同去。和大家一样地系上一个白粗布的大围裙,把下边长长的两个角往上一叠,掖在腰间,摘下的棉桃全都塞进围裙里。我们同声唱起赞美神的诗歌,一同收获着神赐给的福份。我都没想到自己摘得这么快,一会就跑到她们前面去了,收工回来的路上,姊妹们都夸奖我能干,说“袁老师,你真行!手真快!”我回答说“我其实什么都不会,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教会我很多生活上的学问。”北散湖的村外有一大片枣树林,让我感受到最为惬意的就是秋天刮过风以后,我和村里的姊妹们在欢笑中结伴去那里捡枣子,可以捡到很多很多,回来大家一起洗了吃。 是神藉着变化不同的环境,把那曾经无知任性的小女孩磨练成他心意当中的婢女!把那原本无用的雕刻成他手中合用的器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hef.com/bhfz/5778.html
- 上一篇文章: 提高免疫,抗击病*,百合益生菌一直在前线
- 下一篇文章: 地理标志产品价值榜出炉,兰州百合品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