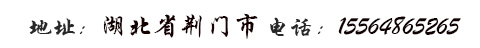流泪谷中的百合花十九
|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十九 回到北平的家里,相忱还和在天津葛沽时一样,照旧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祷告,读经;然后骑自行车去远东圣书学院上班,一般情况中午都会回来吃饭,饭后再回去上班,下午五、六点钟下班回家。 大多数有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读经灵修,即使和我说话也都是说主里的事,其他的像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从来是绝口不谈,也没有提议我们俩出去游玩。 正是在这个时候,相忱陆续给我讲述了他蒙恩得救的见证。 相忱十三岁的那年,父亲把他从天津外公的家里带到北平,同样也是为了学习英语的原因,把他送进位于东城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学校,读小学四年级。在那里,相忱首先遇到了萧安娜老师,虽然他从萧老师得到了无比的关爱,却不肯接受萧老师传给他的福音,因为在他心里想的是:我在课堂上听听《圣经》教训就够了。我不能相信这外国人的洋教,我还要光宗耀祖,做国家的栋梁呢! 不久,又有二位叫石天民的老师来教相忱的国文课,和萧老师一样,石老师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而且是王明道先生的亲密同工。他也很快喜欢上了相忱,热心地向他传福音,为此还专门带相忱去王明道先生的会堂听道,就是这样,相忱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0年前后就初次结识了王明道先生,当时王先生还在外面租房子聚会。开始相忱本不情愿去,只是碍于萧、石两位老师的面子才勉强去的,所以每次总是远远地站在最后面,看著王明道先生在台上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对他所讲的那些内容却很是不以为然,他想:别看你讲得那么好,讲了半天都是空话,都是在说天书!根本就没有神,你讲得再起劲儿也还是没有神!还有王先生在讲道中对罪的指斥也让相忱听起来挺不舒服,他觉得王先生说的也太玄乎了:一个小孩子,也没犯什么大错,又没被法院抓进去,怎么就会有罪呢?!还说每个人都犯了罪,那为什么法院没把每个人都抓进去呀?!既然没有被法院抓进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他总是从所听的道中找出各样自以为是的“破绽”来抵挡和否定福音,甚至看着前面那么多正在聚会祷告的人,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愚昧,太可怜了!科学一天天地发展,人类的思想也会一天天地进步,再过几十年,等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会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时身上的那些顽皮和任性已经渐渐褪去,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个学习认真、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在学校里还被选为班长。一九三0年秋天,十六岁的相忱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校里升入初中。此时,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在身体上和思想上都充满活力的年青人。除了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之外,他又喜欢上了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样样在行;也爱出风头,热衷参加学校的各类公开活动,比如英语演讲比赛什么的,总能找到他的身影。说起那次得到全校第二名的英语演讲比赛,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相忱的脸色上还略带些许不服气。在萧老师的悉心调教下,他的英语非常优秀,口语和发音也很出色,相忱说只是由于他的噪音不够洪亮,才在比赛中屈居第二。在这件小事上,我看相忱实在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又很有上进心的人。 相忱对我说,那时他也和身边其他的年青人一样,努力尝试用自己的思想模式来解读自己的人生,希望通过自己的眼光在世界中为自己找寻一条出路,一个方向。三十年代初期,中华民国在经历过长期的战乱后重新归于统一,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正在大行其道,身处这个大潮流中,相忱也很时髦地成为三民主义的追随者。时任青年会学校校长的蔡八全先生是国民**员,他看相忱对三民主义有如此热心的追求,就对相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吧。”但这事终因相忱年龄太小才搁置不提了。相忱说,他当时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相信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才是他理想中的救国主义。他在课余大量地阅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一一《总理遗训》、《建国大纲》、《中山全书》等等,都逐一地细读过,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可以背诵下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原来的“相臣”改成“相忱”。 以后,我有好多次听到相忱在他的见证中,坦承他那时因为存着刚硬的心,拒绝神的呼召,而使自己的心灵陷入更深的迷惘,以致绝望之中。他不停地涉猎各种书籍,也不停地思考,但有三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答案。第一个是他无法解决自己心中莫名的烦恼,那种烦恼总是困扰着他,使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甚至想要自杀。他一次次地反观自己的生活环境,实在找不出烦恼的来由,但这个烦恼又确确实实地无时不在折磨着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和长辈都很对他疼爱有加;当时父亲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了,生活上丰衣足食;他自己的读书成绩一直很好,和老师、同学相处得也算融洽;因着父亲在电影院做事的缘故,他还可以随便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在这般无忱无虑的环境当中为什么还会有烦恼呢?相忱自己也不明白。有时他被这种烦恼搅扰到不能自拔,甚至想到以死来解决。有一天下午,他照着从书上学来的样子,双手各拿一根大铁钉子准备往电源的插孔里插,就在双手伸向电源的那一刹那,忽然仿佛有一个声音从心里响起:“袁相忱,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父母吗?!难道他们就白白地养你一场吗?!”伸向插座的双手虽然缓缓地收了回来,但心中的烦恼却丝毫没有减少。 第二个问题是:自己如何才能胜过罪恶的引诱,过上一种圣洁的生活。他亲身感受过自己的家庭被罪恶所苦害的伤痛,也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是何等的纯正刚毅,可一旦踏入社会马上就不由自主地被罪恶同化掉了,迅速地在大染缸里腐化堕落下去。他深深地恨恶罪恶,不肯在其中随波逐流,渴望自己将来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在这个充斥着邪恶败坏的社会中做一个清正的中流砥柱。石老师和萧老师在渴慕圣洁的相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忱说他发现这两位老师与学校里别的老师完全不同:别的老师言谈行为随便,他们两位却恪守规章又待人恭敬得体;别的老师课下就是聚在一处吸烟聊天,他们两位却从不参与那些粗俗的闲谈,下课后就认真地备课;别的老师有时对学生急躁甚至粗暴,而他们两位却一向亲切和蔼;别的老师时常会发点牢骚,可他们两位却常常满有喜乐平安。年轻的相忱十分喜爱石老师和萧老师,他能感觉到这两位老师实在与别人不一样,但是又不明白为什么。其实相忱自己也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潮流无异于以卵击石!那么,圣洁生活的出路到底何在呢?难道就只有这样绝望下去了吗? 相忱解决不了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怪?有没有灵*?人死以后难道真的就像世人所说的那样“与草木同朽”、“一了百了”了吗?为了找寻存在心里的那份盼望,相忱深陷在迷惘中苦苦地挣扎。他曾经从传统的宗教人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他所要的答案。在当时对社会有较深影响的有两大传统宗教,一是佛教,一是儒教。相忱以他单纯的眼光来分析和判断这两大宗教。在他看来,佛教固然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社会中间有着持续不断的影响,但“消极出世”的人生观与他光宗耀祖、振兴国家的“远大理想”根本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佛教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而儒教却只教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和“三纲五常”之类的事情,丝毫也不提及“将来”和“死后”的事情,这也不能解决他对人死后将何去何从的困惑。他不停地找寻,失望,再找寻……他对面前任何新鲜的观点理论都感兴趣,但任何这些观点理论又都不能使他得到完全真正的满足,他还在不停地再找寻…… 最后,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转向就在身边的基督教信仰。经过教会学校几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萧、石两位老师的引导,相忱对于《圣经》和基督教的教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伦理方面是无比的,是个很不错的人生哲学,但他却仍然坚持那是个“洋教”,是中国人不能信的!后来,相忱在反省他当时那段的光景时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还不相信神的存在,因为他一直顽固地认为,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没有。“如果真的有神就叫我肚子疼吧!”这个无知的孩子继续在用他的顽梗来挑战神的存在,当然神也始终在用他完全的怜悯来宽容人的过犯,没有真的叫他肚子疼,这反倒使年轻的相忱由此愈发自鸣得意地认为:“你看,我没有肚子疼啊,所以根本没有神!” 转了一圈,相忱依旧没有找到他要找寻的答案,他依旧彷徨在极度的痛苦和烦恼之中,心灵的空虚使他生活在一种看不见却可以摸得到的黑暗之中……他苦苦地寻觅,却拒绝接受神一再向他发出的呼召;自己明明是饥渴难耐,却不肯就近面前的生命之水;他知道自己需要信仰,却不相信独一的真神! 然而,“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5:4)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屋外寒风凛冽,屋子里相忱正一个人坐在灯下做作业,煤油灯昏*摇曳的光亮把他清瘦的身影投在墙壁上,勾勒出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大约九点半钟,相忱完成了功课,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忽然,心中一阵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动,一个意念清晰地显明在了他的心中一一真的有神!虽然说不清他的来处,这个意念却是如此的真实而强烈,不是生理学和心理学可以解释的。 从前,他不肯相信神的真实存在,但是现在神已经真实地存在于他的心里,顷刻间就使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相忱立刻拧熄煤油灯,起身跪在地下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存在,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他承认自己真是个罪人,因为他曾经悖逆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创造之主,独一的真神;接着他又一项一项地向神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撒谎、偷东西、欺负人、虚伪、恨人、自私、嫉妒、骄傲、思想污秽等等。他久久地俯伏在神的脚前,切切地恳求神赦免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和罪,使他从罪中得到自由和释放。 祷告过后,感恩的泪水从眼角涌出,心里长久压抑的重担终于随着泪水一齐解脱,那颗一度陷人迷惘惶恐的心也得以进入永恒的安息之所。他相信自己已经完全归入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新生命,不再死亡。当他从地上站立起来,重新捻亮煤油灯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光明了!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相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属于自己新生命开端的日子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后他常对信徒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生过两次的人,一次是从肉身生的,一次是从神生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日,都应当好好记住。”可相忱一向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连他自己肉身的生日也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是在农历的六月。后来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为了方便记忆,就干脆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写成了六月六日。所以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肉身生日的人,但他一辈子却牢牢记住了自己从神重生的日子。 在受洗这个问题上,相忱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未,相忱照例参加了青年会学校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公宴,这是一个任何学生都可以自由参加的晚会,也说不上与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吃过饭后,大家也像往常一样举着蜡烛唱了几首圣歌,这时有一位来自公理会名叫王梓仲的牧师来到大家面前,逐一地给各人施点水洗礼,这位王牧师并没有询问在场的人“谁愿意受洗?”而是直接就为人施洗。相忱当时也受了洗,但他并没有真心相信。 相忱重生以后在真理上非常追求,除了坚持每星期三次去王明道先生那里聚会听道,自己也用心查考《圣经》,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向石天民老师请教。渐渐地,相忱明白了“受洗”的真正含义“受洗”就是表示“老我”的生命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的是耶稣宝血换来的新生命。他回想起一九三一年圣诞节公宴上的那次受洗,认识到那不是真正的受洗,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更不明白受洗的真正含义,并且按照《圣经》里的教训,应该是浸洗,点水洗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就向石老师提出了重新受洗的想法。石老师听相忱这样说非常高兴,又向相忱讲述了当年王明道先生是如何为了受浸的缘故而被学校革除教职,石老师本人也是如何为此自动退学。石老师进一步给相忱讲解了有关受洗的意义,确认他已经真正明白神的救恩,就请王明道先生为相忱重新施洗。一九三三年八月,王明道先生在北平西郊万寿山后的青龙桥,为包括相忱在内的十余人施洗,其中有后来成为宽街堂长老的孟向召弟兄。这是王先生第二次为人施洗,当时拍摄的照片有幸保存下来,相忱就站立在王先生身旁,照片上写着: “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批。”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的人都要进行认真严格的考察,凡要求受洗的都要多次面谈,并且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验,个人没有清楚得救的根本不予受洗。王先生对圣工的严谨态度,给相忱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从受洗这件事当中,相忱开始深入地反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信仰问题。他逐渐看到,基督教青年会在信仰上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严格地说,基督教青年会不是一个教会,只能算是一种社会团体;在青年会下属的学校中,不讲耶稣基督,不讲十字架的救恩,只有“服务同胞”,“改良社会”,以“慈爱、博爱、牺牲的精神”来服务大众。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来自《圣经》中的一句话“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待人,”2这句经文在马太福音20:28以及马可福音10:45当中,都还有下面的半句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3一一这才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正式的名你中冠以“基督教”的字样,但实质上属于“社会福音派”的信仰,就是强调以他们的“社会服务”来取代了悔改赦罪的福音真理。 注:2《马可福音》10:45上,同参《马太福音》20:28 3《马可福音》10:45下,同参《马太福音》20:28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hef.com/bhjz/2719.html
- 上一篇文章: 百合介绍
- 下一篇文章: 百合会员推荐只要能遇见,就不怕姗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