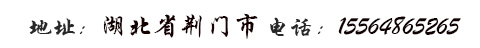读书五月的百合花,联结我们珍视瞬间的化身
| 五月读完舒行的新书《百合花摇曳》,首先感受到的是本书的两重身份。既可以说是自然游记:由北京入春起笔,辗转浙江、安徽、日本;也可以说是博物志:以植物与鸟类为先,着笔约种植物与58种鸟儿。当然,不得不提,它还是一本自然摄影小集。《百合花摇曳》舒行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舒行的行文有自然的诗意。“他大概想不到去年秋天闻见的桂花香味,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时间很短的。这话像是在说人生。”如此闪烁和流淌着冲淡意境的句子,有日常主义先锋诗歌的气质。具体说来,是在语义逻辑和句法结构上都有着入诗成诗的潜力。我总觉得,只要用心探索和深入事物,了解植被、鸟类、水文,大地,聚焦一两个维度,说不定就能理出一部长篇小说的脉络。在《牡丹幽暗》里,舒行写春雨时引出了单词Pluviophile(恋雨者),由此散发的诗意瞬息将我投射到《言叶之庭》里秋月和雪野雨中相见的场景,这是我印象中勾连静谧和荫翳的美术画面,秋月身上轻盈的绿,让人遥想重逢年少时青涩的爱恋。日本是这部自然游记中唯一的异域。而如果以茶为喻,日式文化艺术则似入水之茶,为这剂百合之汤持续灌注着精神底色。比如书中频现的日本作家名字和日本电影:种田山头火、梶井基次郎、松尾芭蕉、泉镜花、谷崎润一郎、清少纳言,以及吉村公三郎的电影《越前竹偶》、小泉尧史的电影《阿弥陀堂讯息》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和她提到的日本电影都孕育着相似的美感。美,应当成为我们的行事逻辑。这难道不是活着的理由?随着生命的铺张,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我们还可能拓展美的边界,借助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或是其他时空的富矿。舒行有百合花,我有鸢尾花。舒行说,对自然,自己必须拓展得更加深远,光有平素的知识和自然表面的美是不够的。现象学的老朋友胡塞尔讲悬置,太多人在有选择地忽略事物,他们以鸟代名,以花代名,以草代名,堆塑起一个个原型范畴,长此以往,形成了相对贫瘠的物种知识系统。准备好深入植物和鸟儿了吗?舒行写道:“忽然有一天,你开始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hef.com/bhyx/14887.html
- 上一篇文章: 赵丽颖的三个百合角色,演绎不同的爱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